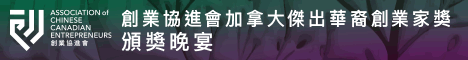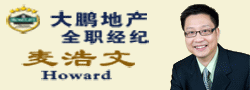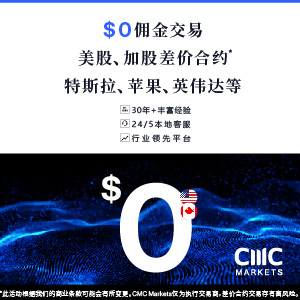7月2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院曾3次发回重审,4次被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奇案”。
天刚亮,法院门前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试图进入法院的旁听者,大部分是4名被告人的亲属以及同村的村民,他们不仅盼来了省高院破天荒的二审开庭,而且更想见到被羁押了9年、生死悬于一线的亲人。
“将死刑判决进行到底”?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以避暑山庄而名闻遐迩的承德市先后发生两起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两名司机被杀,出租车被丢在路边。在此之前,这个旅游城市还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于是,警方在巨大的压力下展开了侦查。
据《承德日报》当年对这一案件的报道,案发数月后,专案组“通过秘密工作”获悉,位于市郊的大石庙镇庄头营村村民陈国清“近来情绪反常,郁闷不乐”。正是这个“郁闷不乐”,使他从此身陷囹圄9年。
当年11月3日至18日,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1996年2月24日,该村另一村民朱彦强也被逮捕。警方认定他们就是抢劫杀害两名出租车司机的凶手。
根据承德市检察院的指控,1994年7月30日杀害出租车司机刘福军的案件系陈国清、何国强所为;1994年8月16日杀害张明则是4人共同作案。两起抢劫杀人案中所劫掠的财物,第一次为300余元,第二次400余元,以及传呼机、车钥匙等。
4被告人称,他们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被迫向公安机关承认抢劫杀人。4被告全部当庭翻供,并且展示身上的伤痕。
承德中院没有理会,径直下达一审判决:“……四被告曾供认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以抢劫罪判处上述4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6年10月6日,河北省高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陈国清说:“第一次开庭时公开翻供了,发回重审后,过两天公安来提审,上绳、电棍、摇电话、下跪,受刑不过又承认了。”
1997年8月12日,承德中院重审后以与第一次判决同样的事实和理由,第二次判决陈国清等4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第二次判决书上没有出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的字样。
1998年2月16日,河北省高院仍然认为事实不清,第二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1998年10月13日,承德中院以抢劫罪第三次判决陈国清等4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两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河北省高院第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0年10月20日,承德中院以抢劫罪第四次分别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4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或许新闻媒体和律师指出了被告没有作案时间的问题,这次判决比前三次更简单,连“1994年8月16日上午9时许”这一无法成立的“作案时间”也抹掉了。
河北省高院在三次发回重审的同时,先后书面提出20多个问题,要求一审法院查证后再做判决。这些问题中包括,4被告均提供证据证明没有作案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承德市第二锅炉厂做临时工的陈国清,考勤簿上的记录和记工员、工友的证言等都证明陈在上班、加班。
承德中院没有理会上述问题,坚定地“将死刑判决进行到底”,从而创造了同一个法院,以同一个事实、同一个理由、同样的法律,将相同的被告人连续4次判处死刑(其中1人为3次)的司法记录!
如此证据
这个折腾了9年,已经严重超期羁押的糊涂案本身并不复杂。事实上,一审法院4次死刑判决所依据的核心证据,就是刑侦鉴定――1994年7月31日,承德市公安局的(94)78号鉴定书说:“双桥公安分局刑警队送来死者刘福军的血一部分、有血迹的刀子一把,经检验,刀子上的血和刘福军的血均为B型;陈国清、何国强的血为O型。”
这天是案发第二日,陈国清、何国强当时既未被抓,也未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也无法证明他们的血液检材是从哪里来的。承德市公安局法医岳红被传出庭作证时说,因为“工作疏忽,将日期写错了”。
1994年11月2日,承德市公安局的一份提取笔录记载,1994年11月2日,从陈国清家中搜出带鞘的自制刀具一把,刀把有血迹。
11月4日,公安部2191号物证检验报告说:“1994年11月4日,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孔庆山送来该市7月30日出租汽车司机刘福军被害案的有关物证检材,要求检验血清型。”且检验报告注明送检的是“单刃匕首一把”,结果是GM23血清型与死者刘福军的血清型一致。
至此,“有血迹的刀子”、“带鞘的刀子”、“单刃匕首”分别出现在这起杀人抢劫案中,其中,只有“带鞘的刀子”与其中一名被告有关联,但案卷中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把刀与承德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先后检验的“有血迹的刀子”和“单刃匕首”有什么关系,也找不到对这把“带鞘的刀子”做鉴定的记录。但承德中院的4次一审判决却认定:“被告人陈国清的作案凶器上发现血迹,经检验与被害人的血型一致。”
至于是3把刀还是1把刀,虽然经历了4次死刑判决,却至今没有查清楚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且刀子被检验后就已经不知去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刀子、血从哪里来的,与被告人有什么关系,这种鉴定结论缺乏科学依据――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说:“不能说刀子上的血是B型,被害人的血是B型,就认定这个刀就是杀死被害人的那把刀。B型血的人多得很,它只是一个间接证据,这种鉴定的证明价值是很低的。即使能够证明这把刀就是杀死被害人的那把刀,还要证明是犯罪嫌疑人拿的刀。”
而在杀害张明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4被告“按事先预谋,各携带刀子窜至市内……”这表明本案中至少有4把刀子,但是,除了一审法院认定从陈国清家中搜出的“带鞘的刀子”是杀害刘福军的凶器外,其他的作案凶器一无所获。
上述问题不过是本案的部分疑点。事实上,刑法学专家们在3年前研讨这个案件时就认为,整个卷宗内几乎找不到能够经得起推敲的证据。
这个离奇的案件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对案情耳熟能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3年前曾参与首都刑法学界对本案的讨论,他说:“多次发回重审,实际上反映了两个理念的冲突――有罪推定还是疑罪从无?对证据的要求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不能把公检法都看成是神仙,什么都能查清楚。法定时间到了,查不清楚,符合法律规定,该放人的就放人。”
(摘选自南方周末,作者:郭国松)